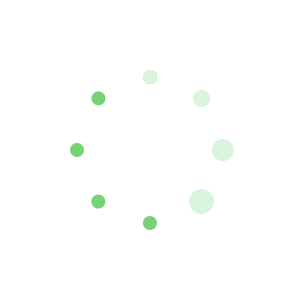前几天从群里看到同学发的关于70后的回忆,思绪一下子被打开了,童年的记忆就如同一首乐曲,丝丝缕缕隐隐约约地飘来,渐渐鲜明起来。
我出生于七十年代北方的农村,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很贫穷的时代,但是我记忆中的童年却是欢快明朗,香甜可口的。故乡四面环水,被几个巨大的池塘包围,我读书后曾查过资料,村子原本的名字叫“巨汪”,方言里“汪”就是池塘的意思。后来“高”姓的人家逐渐发达起来,遂改名为“高立”,在口耳相传中,被喊成了“高里”,于是,这个村名就固定了下来。
小时候,无论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清新,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胜景,在我看来,都是司空见惯之事,都不曾让我心湖里荡起半分涟漪。我印象深刻的是“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后的荷塘,因为那时就可以从池塘里扒藕了。生产队组织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穿着长筒靴子,在黑悠悠的淤泥里扒出来长长的藕,孩子们在旁边欢快地东奔西蹿,有时候能找到鸭子或者是鹅遗留的大大的蛋,或者是坚硬的莲子。能找到鸭蛋和鹅蛋的小伙伴们兴奋的就如同现在中了彩票的彩民,运气爆棚的让人嫉妒啊。而我则木呆木呆的,竟然连莲子和羊粪蛋都不能分清,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个窍门,看到黑色的椭圆状的东西就用脚使劲去碾,如果碎了,就是羊粪蛋,而硌的脚疼的就捡起来,十有八九就是莲子了。
冬天的池塘更是热闹非凡,因为结了厚厚的冰。孩子们就在冰上嬉闹,场面非常火爆热烈。我因为胆子小,不敢在冰面上疯跑,我的弟弟就从家里拿了一个“马杌子”,一种类似于方凳子的座位,但是比凳子的面要宽广的多,然后把它翻过来,光滑的凳子面帖着冰,而我则坐在那四条类似于凳子腿围成的东西里面,任弟弟推着我在冰面上疯跑。如果滑冰去学校的话,绝对比走路快的多。
有的孩子可以在冰上抽陀螺,那时的陀螺不像现在买的塑料和金属玩具陀螺,那时的陀螺都是自己用木头做的,是用长布条做发射器,长长的布条层层缠住木头陀螺,然后猛然松开,因为陀螺尖的部位嵌着一粒光滑的钢珠,所以能在冰面上旋转,男孩们通常大声叫喊着,在冰面上蹦跳着,用布条不停抽打着陀螺,陀螺疯了一样的飞转。
等到孩子们在冰上疯够了之后,就会向着家的方向飞奔,村子里弥漫着烤地瓜的香味,那是我弟弟的最爱,我的母亲通常在炉子上给他烤的热乎乎的,等他回家吃,弟弟总是火急火燎的,所以通常会一边埋怨烤的太热了,烫的嘴疼,一边又“哎吆吆”叫嚷着向嘴里塞。
而我在冬天最喜欢的是地瓜汤。所谓的汤,并不是菜汤,而是稀饭的意思。地瓜汤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用储存的鲜地瓜做原料,一种是用秋天就晒好的地瓜干做原料。第一种是把鲜地瓜削皮切成方块,放入锅中,加上早就用石碾压好的白白的豆面,再添加绿绿的细细的萝卜丝,最后放上水,开锅后放上盐,盛放在粗瓷大碗里。第二种做法是把地瓜干用碾稍微压一下,成了大小不等的碎片,放入锅中,再添加上事先用碾压好的豆钱,开锅后放入嫩嫩的菠菜叶,盐巴,盛在粗瓷大碗中。这种做法的地瓜干和黄豆都不能用碾使劲压,否则时间长了,地瓜干就从碎片变成了地瓜面,黄豆也由开始的榆钱状变成了豆面,那就吃不成了。严格来说,这道用地瓜干做出来的稀饭只有冬末初春的时候才可以做。那时残雪消融,菠菜刚露出几个叶芽,我就迫不及待地摘回家做饭吃。
等到家里的粮食充裕了以后,冬天就有了更好吃的美味。冬日暖阳的时候,我会坐在门口,边晒太阳边啃绿色的萝卜,稍稍的辣意刺激着味蕾,而院子里弟弟会支起来箩筐,逮麻雀,总会有几只傻乎乎的麻雀跳到箩筐下面去吃粮食。我小时候是吃过麻雀肉的,记忆中是很香甜的。那时根本就没有热爱动物的精英们教导我们什么动物不能吃,更何况在我模糊的记忆里,麻雀是属于四害之一,是可以吃掉的。
冬天太阳下山早,夜幕降临,晚饭会从地瓜变成了白面。母亲拿出晒好的豆腐干,放在油锅里煸炒,放上翠绿色的葱花,加入水,开锅以后,用筷子把和好的稀软的面团,迅速地拨到沸水里,一大锅香喷喷的疙瘩汤就出炉了。父亲发工资的日子里,菜偶尔能变成白菜猪肉炖粉条,不过记忆里童年吃的最多的是煎饼里面卷入大葱和腌的香椿芽,有时也会放上腌好的萝卜片,嚼起来咯吱咯吱响,清香可口。如果再把煮好的鸡蛋用筷子压碎,卷入煎饼里,那就更是无上的美味了。
其实小时候的夏天,过的也是快快乐乐的,好吃的东西就更多了。去河边洗衣服的时候,等把衣服晾晒在沙滩上之后,就可以去河里捉鱼摸蟹,也是因为我胆子小,所以去洞里抠螃蟹的活都是由弟弟来完成,而我则是用光着的脚丫在水里慢慢把沙子向两边推,一旦觉得脚底下有被东西硌着或者咬着的感觉,就赶紧弯下腰去,用两只手捧了脚底下的沙子迅速扔到岸边,理论上来说那堆沙子里应该有一种叫“沙鼓拽”的小鱼,可实际上我扔出去的沙子里鱼不多见,贝壳倒是不少。后来我渐渐把这个需要运动能力的活转给了弟弟,而我自己则去沙地里拔茅草根去了。白白的茅草根,嚼在嘴里甜甜的,幸福的感觉也会油然而生。
其实童年的夏天最香甜的记忆是那些鸣叫的蝉。众所周知,蝉是成虫,幼虫叫知了猴。无论是蝉还是知了猴,都是令人口水直流的美味。河边有成片成片的树林,那里就是蝉鸣叫的场所,也是知了猴钻出地面的场所。只要夏天的第一场雨落地,孩子们对蝉的狩猎就拉开了帷幕。松软的地上发现一个小小的洞,有豆粒大小,就可以蹲下去用手抠,抠到可以伸进去两个手指的程度,就停下来抠土,然后伸进去两个手指,十有八九能拽出灰头土脸的一只知了猴。倘若遇到一只反抗精神颇为浓厚的知了猴,它会紧紧扒住土,死活不出来。孩子们会向洞里灌水,不一会,被灌得晕晕乎乎的知了猴就钻出来了。更有调皮的男孩,直接脱下裤子,尿到洞里,和灌水入洞有异曲同工之妙。
像我这种比较笨拙的孩子通常不能灵敏地发现洞口,进而抠出知了猴。我就用守株待兔的笨办法,夜晚拿着灯去照树,照样能捉到不少爬到树干上的知了猴。
等到知了猴变成了蝉,我和弟弟就会合作去捉蝉。弟弟负责粘蝉,他扛着竹竿,竹竿的顶端是粘粘的面筋,而我则拿着袋子,把粘住的蝉取下来,放入袋子里。虽然水边,沙滩上,路边都有树,柳树,杨树,榆树,槐树,各种的树。但是根据我的实践,水边柳树上的蝉要比其他地方其他树种上的蝉多很多。而且,一天之中,正午时间段的蝉最容易捉。所以,童年记忆中夏天的正午,我和弟弟在水边柳树下举着竹竿的记忆最清晰。
无论是知了猴,还是带翅膀的蝉,在母亲的手里,都会变成瘦瘦的肉,加点绿绿的辣椒,最后变成了桌上的荤菜,可以大快朵颐。
其实夏天也是有素菜可以当加餐的。频繁的雨水会让腐烂的木头生出来密密麻麻的黑色的木耳,我通常会细心摘下来,交到母亲手上。只要找到腐烂的木头,就一定能寻到木耳,而且,只要几场雨下来,被摘空的木头会继续长出木耳,颇有春草的那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的生生不息的感觉。
如果树林里找不到木耳,我就会到池塘边,寻找一种叫做“地皮”的东西。雨后,池塘边的地上,石头上,会披上暗绿色的衣服,远处看是一大片暗绿色,走近的话会发现那是一朵一朵的类似木耳的东西,只不过颜色不一样罢了。等我熟悉了以后,就渐渐发现了“木耳”和“地皮”的区别。除了颜色之外,厚薄程度是不一样的,前者肉肥厚,后者是稀薄,前者吃起来有韧性,后者嚼起来有“咯吱”的声音。但是无论如何,这些素菜都让我们夏天的饭桌变得丰富多彩。
至于丰收的秋天,则是五谷丰登,瓜果飘香,连空气都变得香甜。
就连记忆中应该青黄不接的春天,也因为有了肥硕的榆钱和芬芳的槐花,酸甜的桑葚,而变得美味可口了。
童年,在我的记忆里,芬芳宜人,香甜可口。我仿佛看到,那些熟悉的美食,带着浓郁的香味,穿越过时空,微笑着向我走来。
散文精选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