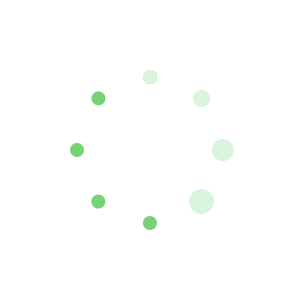我经常的失眠,不是睡意全无是离奇恍惚的万事万物蜕化操纵我的梦境。在阳光明媚的早晨,不肯醒来。像个婴儿,无法执著地分离似梦非梦的东西,只能看着它们,肆无忌惮,仿佛五彩斑斓的蝴蝶。能隐隐约约的听见附近厂子里机器的蜂鸣声和一堆鸟声。
卧室的床很大,如果愿意纵横皆可安睡。我曾经对女友说这里纵向可以睡下三个壮年人,横向凑合一下可以变成四个。没有想到她白了我一眼,理直气壮地指着我的鼻子,指责我是异想天开。后来她去了银川,剩我在家。经常躺在床上接她打来的长途电话。语言软弱无力。觉的自己很颓废,像成年女人一样。通完电话,发现自己的头发和眼睛像一株枯萎的植物。身体散发着味道,粘稠而又失重。习惯看手机屏上的时间,绝望地让时光从指缝间偷偷溜走,然后再闭上眼,再睁开。随意地抓起床头柜上的书,任意地翻动,不管情节和文字。
在客厅走动的时候觉得很孤独。拖鞋和木地板摩擦的声音,时而芜杂,时而沉闷。阳台的对面是厂房的后院,很多的工人在劳动,往来行走,面无表情。打开窗户,就会有无数的新鲜的空气进来,争先恐后很让人感动。从阳台可以看见卧室前面一棵繁茂的榆树,高出厂围墙三米。树冠和枝叶使我想起前年央视春节晚会的千手观音。婆娑而妖娆,妩媚而高雅。所有的玉手纤纤扬起,并蒂连根,天荒地老。 有一群喜欢喧闹的麻雀们在枝叶间跳跃,却没有一只肯飞进房间。让我惆怅。榆树下是一地碎了的白花,像一场散了的风花雪月。勤劳的人在空地上开垦出的土壤里劳作, 有小孩在周围嬉戏。
阳光炫舞,很热闹地跑到厨房大理石操作台上。整个楼房是坐北朝南的布置,阳台和卧室被东升的太阳冷落,所以一般受宠的时间放在午后。我习惯了在卫生间里洗漱的时候放几首歌,是音响效果很好的流行音乐和几首过时的民歌。心里不停地潮湿,感慨生活原本就是不停的释放和享受。如果心情好就会合着音乐节拍清唱,如同走在天南地北,没心没肺地流浪。我用铝壶在灶上烧水,兴奋地泡铁观音或者冲咖啡,千方百计给肠胃一个交待。
翻看日历的时候发现今天是2007年6月1日,20年前的今天我打算和同学去很远的地方野炊,书包里是妈妈给我煮的鸡蛋和用粗糙的碗盛的凉面,家境好的同学会大方的带上煮熟的牛肉。通常那是一个阳光和心情很好的早晨,小草带翠,树木展绿,鸟语花香。
下楼的时,看见单元门前的草坪里有人拖着长长的管子浇水。三四个退了休的老人在草坪对面围在一起下象棋,激烈的争吵,像打仗一样。棋子乱飞,硝烟弥漫。一个小孩骑着童车在小区的水泥路上飞驰,最后熟练的停在健身场里。独自一人在那里沉思,像一个哲学家。不断的有人迎面走来,老人、妇女和小孩,他们的脸上有着发自内心的微笑。令人欣喜。年轻的母亲怀抱小孩,沐浴在阳光下。晨练的时间已经过了,但仍然有老太太在那里扭腰和行走。
大街上汽车来回奔驰,继而在我的视线中模糊、消失。陌生人跨着包或者抬着东西和我并走,偶尔彼此相望,擦肩而过。仿佛忙碌的蚂蚁。时间不停地飞逝,我坚信生活是一双眼睛,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平淡、真实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