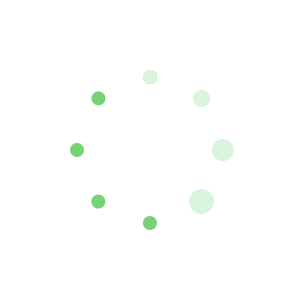元宵忆亲
陈白尘
前几天是元宵佳节,一连几天,电视屏幕上出现各处灯节的盛况;报纸上也刊载各地“闹元宵”的报道和照片;这是三十多年来未曾见过的、发自农村人民内心喜悦的反映!
但人到望八之年,总不免有点“九斤老太”的脾气:老觉得他记忆中的东西更美好。我在许多镜头和照片上曾细细寻觅每一只灯彩,但没找到一件超过我记忆中、或者说我半幻想中的那一架精巧、美妙的走马灯!这说法自然有“今不如昔”之嫌,可不美妙!但我的动机还是自以为美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我也是父母所生所养,尽管他们都已作古五十年,但触景生情,偶然想念起他们,也属人情之常。况且他们都是平民百姓,绝无在他们头上画光圈之意。
当我五岁的那年,我们家搬进清江浦城里住。地点在东门大街上,自然也没有门牌号码。按照当时商店习惯,应该称“纪家楼西、大源巷东、鼎吉祥绸布庄对门,坐北朝南便是。”因为我父亲那时——即辛亥革命后一年,也确实生活好了些,自己开了店铺。家,就在店铺后面,有三间堂屋、两问厢房,也都是瓦屋了。我家那张全家福的照片,估计便是这时候照的,也是家庭转入小康的证据。但我这时最寂寞:三位哥哥,最小的也比我大八岁,而比我小六岁的妹妹尚未出世;当时既无托儿所、幼儿园之类设施,又未到入塾读书的年龄,整天只好在家里东翻西找,爬上爬下,想寻觅些可资消遣的物事。有一次,以偶然的机会,被我爬到东厢房的阁楼上去了,这可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那么欢喜!因为这儿都是我当时见所未见的东西,虽然不过是些破烂。比如一顶没有顶子的红缨帽,一串断了线的朝珠,一两个断了胳膊、缺了腿的陶俑,几本一尺见方的旧帐簿子,一两把破损了的宫扇等等,等等。其实,那时候连这些东西的名称我都说不出来,更不知道其用处何在了。只有一张案板,足有如今乒乓球台那么大,我勉强算是认识的;但那又是做什么用的呢?如说是厨房用品,没有那么大,也不至于涂上朱红漆;要说是桌面,我只见过圆的,哪有长方形的呢?真是纳闷!第二天黎明起身,我母亲又按习惯将我从床里拖出来,坐在她怀里。她披上棉袄,下身捂在棉被筒里,开始她早晨的训子课了。这便是讲“古记”。——古记者,我们清江人讲故事之谓也。她的“古记”有两大类:
一是讲《三国》、《水浒》、《西游》以至((红楼梦》,后来她成为我接触文学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但我在五岁以前,未免是“对牛弹琴”,我还不能领略;另一类则是讲她幼年“逃反”——即什么战争中逃难的艰苦经历。老实讲,听腻了,也不好听,正如现在青年对于忆旧社会之苦不感兴趣一样。而我也同于一般孩子:爱对不懂的事寻根究底,便提出问题:“阁楼上那些东西叫什么,是干什么用的?”等等。谁知引出一顿责骂:“谁让你爬阁楼的?以后不许再去乱翻!”我当然只有唯唯听命。但孩子的好奇心是禁止不了的。有一天我又偷偷摸上阁楼,索性再看个仔细。这一次,可大有收获:就在那厚厚的大帐簿里翻出许多许多一寸多长的小纸人儿来。这是平面的剪纸,可是用厚纸裱过的。这些人物我大都认得,是孙悟空、猪八戒、唐僧师徒们和一群虾兵蟹将,以及另一个老和尚,似乎是法海;前者是《西游记》无疑,后者可能是《白蛇传))中人物了,可缺少白娘娘和许仙,只能存疑。但奇怪的是,这些人物的手臂、腿部、腰部和颈部都可以活动,而活动部分是用白棉线钉了的,因此他们都可以做出各种动作来;有如今日剪纸的动画片里的人物!这不禁使我赞叹而惊奇!这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为这些色彩鲜艳、栩栩如生的小纸人儿入迷而沉醉了许久许久,不肯离开阁楼。忽然,母亲在叫唤了:“四儿!四儿!你在哪里?”我只得捧着这一大堆小纸人儿走下阁楼。
这自然又引起一顿责骂:“你又爬上去了?”可我撒娇放赖,偏要追问个不休。“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幼儿”嘛,母亲拗不过。只好一一回答我的问题。在这一问一答之间,可勾画出我父亲过去半生的奋斗史来。原来我的祖父一一对不起,至今我也说不出他的名讳来,因为在我降生之前很久,祖父和祖母都去世了一一是在一家钱铺的店员,因此我父亲十多岁时也进了钱铺当学徒。三年满师以后,他开不了店铺,却去当了裱画匠。原来在他当学徒的钱铺隔壁,有一家裱画店,他每天都去裱画店里偷看字画,同时也就偷学了裱画的手艺。母亲说:“阁楼上那张红漆案板,就是裱画用的!懂了吧?”我问:“他也会画画儿么?”她说:“那些破宫扇上山水人物,不就是他画的么?”并且不无自豪地说:
“他呀,也真能干,学什么都一学就会!”但又摇头:“就是没长性!”
我为自己父亲居然会画画儿而自豪起来,于是很得意地反问:“那这些小纸人儿也是我大画的了?”这里的“大”字应读平声,即父亲之意。我们清江浦的老百姓在口头上从不拽文称“父亲”的,至于官宦人家如何,不得而知,它是否是“爹”的音转呢?未必。因为我们对祖父才称爹的。《金瓶梅》里好像称父亲为“达达”,颇为近似,但也不知所据如何了。故我只从乡俗。
“自然是他画的!”母亲很得意地拂然说。
“那是做什么用的?”我追问。
“你不虚!昕我说嘛!”她歇口气,又说:“你没看见那红缨帽、朝珠跟泥人儿么?”
原来我父亲裱字画缺助手,又歇业了。他的朋友丁四和丁六都是开古董店的,劝他入伙,但干不到半年,便退伙了。他说,卖假古董损德,而真古董要刨人家祖坟,更损阴德,不干!于是又向纸扎店偷学了手艺,平常扎些纸人纸马糊弄鬼,过年就扎些灯来卖钱。
说起灯,我完全懂了:兔儿灯可以拖了走;西瓜灯可以在地上滚;马儿灯更可以扎在腰里奔跑;还有那举在手里的,叫“四老爷打面缸”的,它是个白鼻子小丑,泥做的脑袋,可以一摇一摆作点头晃脑的姿态,是我最喜欢的!我便央求说,今年过年请我大扎个‘四老爷打面缸’吧!
“那算什么?”妈傲然说:“你大才不扎那种灯哩!”
我自作聪明地说,那一定是走马灯!我看过的,有“三英战吕布”,有“关公过五关”之类,可那很贵,我大肯扎么?
母亲依然不屑地说:“那种走马灯又算什么?”她指着我面前那一摊小纸人儿说:“这才是你大扎的走马灯上的人儿!”
我看这小纸人儿比走马灯里那些人物要小,便问:“这么小?”
母亲哈哈大笑了,用手一比,比现在二十四时的电视机还要大:“这么大!你哪见过?”接着她说,灯面上糊了白纸,不像普遍走马灯,纸人儿在一个门洞里跑来跑去兜圈子;这些小纸人儿有几十上百,都站在白纸上打仗。比如“水漫金山”吧,金山寺山门口站着法海和尚,一手挥拂尘,一手举禅杖;白娘娘率领一大批虾兵蟹将和一大群天兵天将在水上大战,那不是上百人么?
我当然叹为观止了。但这些小人儿怎么能站在纸面上?他们又怎么会打仗呢?据母亲的回答是:那些小人儿其实是粘在上面的:先用高梁秆子的细芯(取其轻),剪成一二分圆柱体,一面粘在纸上,一面粘在纸人儿的腰部,便似悬空地站在纸上了。至于会打仗弄动作呢,那是在小纸人的头部、双臂、双腿上都系上一根头发,每根头发都又穿过纸面,汇总了系在风轮上;灯里点燃蜡烛,推动风轮,于是整个灯面上的人物都活动起来了!这也就是那些小纸人儿关节上都钉上白线之故了。至此,我更惊叹不止。
但我又追问:“现在我大为什么不扎了呢?”
母亲叹息了:“一架‘水漫金山’灯也好!孙悟空大闹天宫也好,要做上一个月,如今谁买得起呀?”
“以前卖给谁?又卖多少钱?”“一架灯要卖几石米。你大和你大哥两人只能带上三四架灯,还要坐船到扬州去赶灯节,那里盐商有钱,才能买得起。可如今扬州也不行了!”接着是一声长叹。
看过今年各处灯会,我也发了一声长叹。我父亲是生不逢辰;如果他生在今朝,就凭他的灯彩,也许会成为一位工艺美术家吧?更恨余生也晚,如果我能学到他的那副好手艺,岂不也可以为今年的灯会增添光彩?
不过我父亲虽不是什么工艺美术家,但他一辈子做商人,也颇有些“艺术家”的风度。这就是我母亲说的“没长性”。他此前学过钱铺生意,裱过字画,卖过古董,又扎过灯彩等等,都是爱好。此后,他开过小钱铺,那是他本行,不久,他又开酒店,因为他爱喝两杯;后来,我的哥哥们都学了织袜子的手艺,他又对这机器感兴趣,便开了个家庭作坊,美其店名日大纶袜厂。其实并无厂房,也无工人,除了为儿子就业,也为我表兄、表姐们学点手艺。以后,店铺交给儿子们管,他自己却去养菊花、养金鱼,自己做山石盆景以自娱。晚年,袜厂营业日衰,终至顶替出去。他便携带孙儿、孙女去“文元”听王少堂说《水浒》。他平易近人,从不发愁,街坊邻里都称为“陈大爹爹”;文雅点的,就称之为“鹤翁”。他爱说笑,有幽默感;遇事马马虎虎,不太认真;即使对儿女不满,也未见他严厉谴责;晚年更不讲穿着,一件马褂,四季不离身,老友们在背后又称他为“陈大迷妈”。迷妈者,即马虎之意。只有一桩,到晚年老两口不太和睦;母亲卧病在床,常常提名道姓地骂他,他也只退避三舍,和邻居打哈哈去了。对于这点,我是不免腹诽,觉得他有点无情了。
可是不然。当我母亲病逝之后,他不仅尽可能地厚殓她,而且亲自动手,在灵柩当头刻上一行宋体朱字,其刀法之工整,不下于篆刻专家。这件事,可使我回忆起幼年时母亲对他的赞誉:“他学什么都是一学就会!”可是他几时又学过刻字的手艺呢?到了出殡日期之前,他说不要向杠房里租什么“龙杠”或“如意杠”了,也不用绣花的棺罩,只租一副棺罩的竹架。然后他去东乡买了三担扁柏枝叶来,又买了一整圈细铅丝,然后便叫我当下手,在竹架上编出一只翠柏棺罩来;而且顶罩的四角还高高翘起,有如宫殿的模式。之后,他又自己动笔,画了八个尺多长彩色人物,用纸裱糊好,然后一个个剪下,原来是“八仙过海”!不用说,它们和上百朵白色的纸花,都是装饰在翠柏棺罩上的了!邻居们看了都赞叹说:“啧!啧!啧!这世上谁见过这样美的棺罩!”可父亲摇摇头说:
“还没完工哩!”
两天以后,即“开吊”的前夜,更大的奇迹出现了:扎好的翠柏棺罩竖立起来了,而且在棺罩的顶上挺立着一只屈其一足而翘首长鸣似的丹顶鹤,真是亭亭玉立,栩栩如生!这正是我父亲紧闭在他卧室里两天制作出来的艺术精品!
出殡的那天,作为“杖期生”的父亲全身缟素,手持丧杖,走在我们这群孝子孝孙行列之前。我隐隐听到他在嘤嘤啜泣,想到棺罩顶上那轻轻摇动,仿佛振翅欲飞的丹顶鹤的姿态,又联想到他的“雅篆”正是“鹤亭”二字,不禁泪如泉涌。我想,他应该是位“艺术家”了,因为我从他在丧期中的几件小事看出一个“艺术家”的灵魂和他深挚的爱情。母亲死而有灵,也该含笑于九泉了吧?
1984年2月25日
点击图片可阅读《谈父亲》图书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