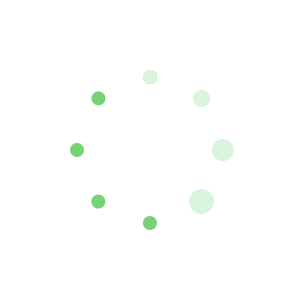珍珠鸟
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
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
我把它挂在窗前,那儿还有一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我便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小绿叶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从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
阳光从窗外射入,透过这里,吊兰那些无数指甲状的小叶,一半成了黑影,一半被照透,如同碧玉;斑斑驳驳,生意葱茏。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从绿叶中伸出来。
我很少扒开叶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
3个月后,那一团愈发繁茂的绿蔓里边,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儿。我呢?决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小脑袋从叶间探出来。更小哟,雏儿!正是这个小家伙
它小,就能轻易地由疏格的笼子钻出身。瞧,多么像它的母亲;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后背还没有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儿。
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绳撞的来回摇动,跟着跳到画框上去了。只要大鸟在笼里生气儿地叫一声,它立即飞回笼里去。
我不管它。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决不飞出去。
渐渐它胆子大了,就落在我书桌上。
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嚓嚓响。
我不动声色的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意。这样,它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角质的小红嘴,“嗒嗒”啄着我颤动的笔尖。我用手抚一抚它细腻的绒毛,它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
白天,它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它就在父母的再三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
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呆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扒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脚刚好给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抬一抬肩,它没醒,睡得好熟!还呷呷嘴,难道在做梦
我笔尖一动,流泻下一时的感受:
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时光
一岁将尽,便进入一种此间特有的情氛中。平日里奔波忙碌,只觉得时间的紧迫,很难感受到"时光"的存在。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然而到了年终时分,时光的感觉乍然出现。它短促、有限、性急,你在后边追它,却始终抓不到它飘举的衣袂。它飞也似的向着年的终点扎去。等到你真的将它超越,年已经过去,那一大片时光便留在过往不复的岁月里了。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蒙?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
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做"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叫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
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不管这些事情怎样庞杂与艰辛,无奈与突兀。我更想从中找到自己的足痕。从春天落英缤纷的京都退藏到冬日小雨空?的雅典德尔菲遗址;从重庆荒芜的红卫兵墓到津南那条神奇的蛤蜊堤;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中;究竟哪一些足迹至今清晰犹在,哪一些足迹杂沓模糊甚至早被时光干干净净一抹而去
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它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当、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
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
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
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得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惟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
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
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
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
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
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惟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不再那样咄咄逼人了。
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我写《散花》
有人问我如今在奔波於四方的文化抢救中,如何写作,有没有固定的写作时间,是怎样一种写作习惯与方式。我想了想,说:——散花。
我心中最优美、最浪漫的动作是天女散花。她以最好的心情,最大的爱意,最优雅的姿态把缤纷的花随手抛撒,五彩缤纷的花朵裹同衣袂飘带一同飞举;芬芳的花雨纷纷扬扬落向人间。欣赏天女这样做,只是表达一种心愿与情怀,并不刻意於其它。
我的写作终於也尝到这种滋味。不管人在哪里,在忙什么,只要心有触动,笔有情致,就会从心中飘出一朵花来,落到纸上。时间虽少,但时间是最灵活的,到处可以找到,也随时可以安排。我喜欢托尔斯泰在《复活》篇首所写的春草从城市的砖缝里拼命钻出来的感觉。写作是心灵的渴望。作品是生命的花朵。它是不可抑制的。它随时随地产生。只要放开手脚,信由着它,就会随时开花,随手抛撒,像我一直神往的天女散花。
于是,我将我这本新书取名为《散花》,所收篇目乃是近三年中所写上百篇作品之自选。其中小说三篇,从2006到2008,每年一篇。这样做并非我着力延长个人的“小说创作史”,而是当今我的写作,短的小说尚可为之,长的小说不可为之。
其余则是两大类,一是散文,无论写人写物,大都是有感而发,抒写一己情怀;另一是随笔,一概是对文化时弊真刀真枪的火拼。这两类截然不同的文字正符合我的两种写作主张:一是心灵写作,一是思想写作。
还有一部分是与画相关的散文化的文字,这种另类的文体我随手写了不少。是思绪或情绪的片段,也是散文的片段。其实无论於人於文,片段才是精粹。我作画总是缘自一种特别的心境,或把过多情思投入其中。可能出於我的另一种——作家的习惯,每每画过,还会把作画的缘由和种种心理写出来。作家的天性是挖掘内在的精神与深在的心灵,於是这种写作已成我专有的一种文本。
再有,我把这本集子取名为“散花”,还想表明我现在的写作心态。我不再像年轻时候把写作当做一种攻尖,我已经没有写作之外的任何追求了;换句话说,写作是我纯粹的心灵和思想的随心所欲。
如果谁能体会到我这种写作的本质,我便视谁为知己。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