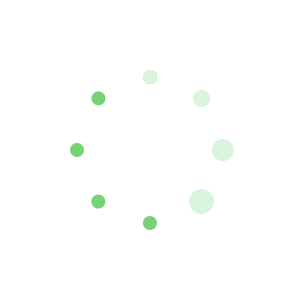小卖部的南墙外,有一株小碗口粗的歪脖儿杏树。每到麦子拔节抽穗的时候,那杏树便在青绿的枝叶间,挂上许多青青黄黄的小杏儿。
不冷不热的天气里,总有一帮退休了的老头老太太,坐在树下打扑克,见天儿仰着脸,瞅着树上的小杏儿,砸吧砸吧嘴里渗出的酸水说:“快到麦收了,杏儿也该熟了。”
那一年,已是过了清明,开满了一树的杏花,白色带着微微的粉红,像少女娇羞的脸。花瓣儿中间,有着几根紫色的花蕊,沾着些明黄的粉粒,引得蜜蜂尖着屁股使劲地往花心儿里钻,嘤嘤嗡嗡地喧闹着,蜂儿惹了一身的黄粉,那透明的翅在阳光下折射出点点的亮。
杏花儿开了,比往年开的都繁茂。再经过辛勤的蜂儿作媒,朵朵新嫁娘将会孕育出一个个美味的甜杏来。
以为过了早春的料峭,便不再会有寒的摧残,谁知,一夜的雪竟与满树的杏花争艳。绒朵儿般的雪团,迫的花容失色。将片片花瓣化作泪滴,飘飘洒洒地落了一地。
毕竟到了春的季节,那雪勉强地露脸,不到中午,便悄无声息地遁去,湿润了杏树粗粗细细的枝干。那些原本是花苞的蓓蕾,少了许多的拥挤,反而开的更加旖旎动人。
就是这个杏花开放的季节,就是这个春雪不按套数出牌的早晨,硕琪死了。死在春暖花开的时节。
几年前,硕琪退休回家。没有了工作的繁忙,反而一下子适应不了闲散的日子,突发脑梗塞。幸而发现及时,住了些天医院。除了走路较往常脚步迟缓了些,恢复的还算不错。
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大了,各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硕琪便和老妻一起过起了二人世界。硕琪的人,长的没说的,一米七几的个儿,不肥不瘦的身材,五官相貌看得出当年的英武帅气。他那老妻,与他挺般配,细高挑儿,举止端庄得体。邻居们便时常看到硕琪拖着迟缓的步履,往返于后街那条水泥道上。遇到相熟的,便举起一只手,算是招呼。而对方因晓得他的病,也点头回应,粗略地说一声:“老表,闲溜哪?”陪侍在身旁的老妻,也便笑容可掬地多说几句寒暄的话,时不时地用那深蕴了两潭爱意的凤眼,融融地看着老伴那已经养的很红润的面。
只说是硕琪带病延年,只说是相携到老。谁知出人意料的,倒是那端庄贤惠的老伴突然撒手西去,撇下痛不欲生的硕琪,立马儿身子矬了一大截,脚步更加迟缓,见人也呆呆儿地没了生气。
偶然的闲逛,硕琪到了那个小卖部旁,杏树下老头的老太太,都是公检法部门的同事及家属,原本是熟识的,便热情地邀他歇歇腿。
硕琪似乎被那群人的快乐所感染,也便稠了拜访的次数,也便倾倒了自己的苦衷:“唉,儿女双全,却各回各的家,各有各的事,有人做饭吃,有人洗衣服,却没个说话的人。”
那些老太太们中,便有热心肠的,要为硕琪找个伴儿。
谁行的善事,不知道。但不久传出的消息,硕琪每天晚上必走上几里路,去最热闹的恩华药店广场看跳舞。跳舞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硕琪不会跳舞,但他总是站在固定的地点,目光锁定那个固定的女人。
那女人,是个退休教师,年过半百,虽是半老徐娘,但风韵不减。细高个儿纤纤腰,白净面皮弯眉稍,举手投足风拂柳,春风妩媚老来俏。
硕琪醉心于女教师,女教师在舞的同时,也不忘时时回他一个笑,四只眼珠儿拧成绳,擦出电。
这对知味的过来人,很快地谁也离不开谁。硕琪便思量将她娶回家。没想到,刚提了个头,儿女们便一条声儿的反对,儿子说:“爸,你都多大了?安稳点行不?缺你吃还是少你穿了?不要女人不能过怎么地?”儿媳妇儿一脸鄙夷地说他是“老不正经”。
硕琪蔫了些日子,实在憋不住相思,便学着年轻人离家出走,与那女教师在外租了房子另住。
听说,两人的小日子过得挺恩爱。女人为男人做可口的饭菜,男人天天的陪着她去广场,如痴如醉地瞧着她跳舞。
家里的那群白眼儿狼气炸了肺,声言:再不回家,干脆将来外死外葬算了。
硕琪的一念之差,便是听信了儿女们的恐吓,担心百年后不能叶落归根。有一天,他独自回家,还想说服儿女,接受那个女人。
一家子关起门来谈判,如何的情形外人不得而知。只是,那天硕琪回到女人身边的时候,据说是神情萎顿,半夜里得了脑溢血、女人一边叫救护车,一边通知他的儿女。但是,硕琪的生命还是走到了终点。
硕琪死了,就在那个杏花开放的季节,就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而他只是被大家谈论了几天,那些叹息便如那场雪,化的无影无踪。
又到了布谷声声的季节,麦黄杏熟了。杏树下的老头老太太们,你一捧,我一兜地分享着杏儿。椭圆的杏儿表皮光滑,闪着诱人的黄色。掰成两半,那纯纯的黄中立时沁出一缕扑鼻的香甜,馋的人不由得舌尖儿渗出水来。
人们已经忘了那场雪,忘了正是那树雪中的杏花,孕育了如此甜美的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