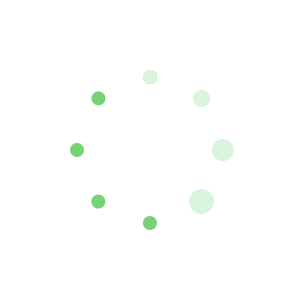【这个老头:篇一】
假期过后,又要去上那个辅导班了。说实话,一个月不见,还真有点想念辅导班老师——那个脸像土豆一样的胖乎乎的老头儿,脑袋顶上竖着零散的几根白毛,好像漫画中的“三毛”。他粗大的手上总是会有白白的粉笔灰,像面粉一样黏在那里,好像他是个磨坊里的工人。他总是好几节课都不换他那粗布衣裳,讲课的时候唾沫星子又细又碎,飞得那个远啊。据说他还是济南市里数一数二的数学老师嘞!只是当面时,我们叫他“陈老师”,背地里,我们都不谋而合地叫他“陈老头”。
每周六,我们都会穿过一个狭长的小胡同,来到一间连桌子椅子都长短不一的简陋教室里学习。听着陈老头激昂的讲课声,我们在卷子上涂抹着几何图形。他在讲课时,如果看见我们在说话,就会用一只布满粉笔灰的手指着自己的眉尖,另一只手冲我们摇来摇去,脸一缩,眉一皱,训斥着:“哎,哎,别说话……”仿佛一个和蔼可亲的奶奶在提醒我们:“哎,哎,掉东西了……”
常常,他在黑板上写错字会直接用胳膊擦,结果一节课下来全身上下都是粉笔灰。到了冬天,我们就开玩笑地说:“呦,屋里多了一个雪人啊!”而夏天,站在空调旁的他,头上不多的白发会被吹起,竖成可爱的弓形,我们就都不听课,只望着他的头发哧哧地乐。
他说他是数学名师啊!——他会把负数比作欠钱,让我们一下子就把计算法则弄得很简单很流畅;把平方比作戴帽子,让我们一下子就记住了那些公式。他说他当过大学里的足球队长啊!——中国男足一出丑他就要在课上大讲:“我带你们去踢都比他们好。”然后同学们就在下面叫好,说,下课踢一场去!
他很自信,会在我们忙着做题的时候慢悠悠地背着手在旁边踱着方步,跟我们讲他的丰功伟绩,就像是一个自豪的农夫在骄傲地夸耀自己的庄稼长势多么多么地喜人。当陈老头嘴里说着“我教出来的学生啊……”,我脑子中的那个农夫就挥舞着锄头站在山头朝着下面喊:“俺的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当陈老头说:“别看咱这房子小……”我就会想象着他朗朗上口地吟诵:“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何陋之有?”然后扑哧一声突然笑个前仰后合,一不小心惊醒了睡在墙角的几只蚊子。
辅导班的陈老头可爱,同学也活泼,风扇也呼呼地刮大风,卷子用三支笔加橡皮压着都会满天飞。风在教室里头跑动。我们就在风声中、忙着捉卷子的风声中,把一节一节的时间度过。
【这个老头:篇二】
黝黑的脸上布满着刀割似的杂乱无章的皱纹,剃不干净的胡扎常年驻留在那油腻的皮肤下,年轮在他的脸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他出生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那时候中国才刚刚成立,而他,不偏不倚地降落在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孤辟的小镇里。那时候的农民没几个受过教育,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中国有句话说得真是好极了,棍棒底下出孝子,他在棍棒下磨练心早已坚硬如铁。
心高气傲的他初中毕业辍学回家后不愿下地干农活,又迫于无奈在社会上需要一片不大的立足之地,便东凑西凑,凭着家里那不多的存款,买了一辆货车,这可是稀有的。拥有自己的一辆车,所有人都以为他家财万贯,他也开始变得飘飘然,自以为戴上了了富贵子弟的头衔,狂妄自大,心高气傲。
有一朋友需要借钱,他们家一贫如洗,他却为了显摆去银行贷款,银行看着他家里有辆车才肯将钱借给他,可惜这位朋友还不起,银行上门讨债,他只得把家里唯一的值钱的东西卖掉,因为卖车的钱是有的是远远不够的。他便在监狱孤苦无依的熬过三个月。
45岁的他自己仅存的本领不起作用,只有干着简单而又辛苦的农活。家里还是得吃饭,他拼死拼活的在一亩三分地的战场上挣扎,他何尝没有农民那样拔苗助长的心情,在骄阳似火的日光下,炽热的太阳似乎把时间考僵,他挽起裤脚,带上一顶。稻草编织的帽子便插秧去了豆粒大的汗水在全身各处上下,在群升,豆粒大的汗水在全身各那健康的小麦色皮肤夹着紧缩的眉毛像没像麻花一样拧起在一起,浑浊的目光里满是无奈,眼角似乎又多了几条了生了根的皱纹,俊秀的鼻子上无端生出了几个麻雀点过的小点,而特别是那干裂的唇,像热狗被烤焦了一样翻卷上去。
他手脚麻利地种着水稻,却不知太阳公公要学西方度假了。便拖着一条带泥水的深蓝色粗制滥造的裤子、疲惫的身体回家。
改革的步伐终于迈进了这股这古风犹存的小镇,年近六十的他,伴随着工地上的泥土搅拌机的声音,也在工地上拼搏着,带着那多病的躯体依然充满活力的惊魂也在工地上奋斗着。上天却不眷顾他,一根高压线压断了他的小腿,他不得不截肢,他以为从此生活失去了希望,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讨债的银行也不让他还了,他也就是安享他的晚年了吧。
如今,他嘴上叼着一支烟,骨感的手颤巍巍的点着,倚着一副拐杖,默默的走向回家的路。
愿他永远健康。
——致最亲爱的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