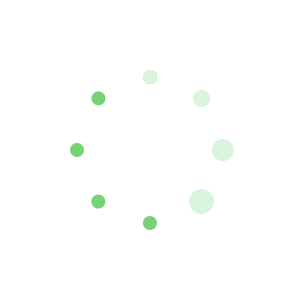《素心笺》:髻
母亲年轻的时候,一把青丝梳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白天盘成了一个螺丝似的尖髻儿,高高地翘起在后脑,晚上就放下来挂在背后。我睡觉时挨着母亲的肩膀,手指头绕着她的长发梢玩儿,双妹牌生发油的香气混着油垢味直薰我的鼻子。有点儿难闻,却有一份母亲陪伴着我的安全感,我就呼呼地睡着了。
每年的七月初七,母亲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头。乡下人的规矩,平常日子可不能洗头。如洗了头,脏水流到阴间,阎王要把它储存起来,等你死以后去喝,只有七月初七洗的头,脏水才流向东海去。所以一到七月七,家家户户的女人都要有一大半天披头散发。有的女人披着头发美得跟葡萄仙子一样,有的却像丑八怪。比如我的五叔婆吧,她既矮小又干瘪,头发掉了一大半,却用墨炭划出一个四四方方的额角,又把树皮似的头顶全抹黑了。洗过头以后,墨炭全没有了,亮着半个光秃秃的头顶,只剩后脑勺一小撮头发,飘在背上,在厨房里摇来晃去帮我母亲做饭,我连看都不敢冲她看一眼。可是母亲乌油油的柔发却像一匹缎子似的垂在肩头,微风吹来,一绺绺的短发不时拂着她白嫩的面颊。她眯起眼睛,用手背拢一下,一会儿又飘过来了。她是近视眼,眯缝眼儿的时候格外的俏丽。我心里在想,如果爸爸在家,看见妈妈这一头乌亮的好发,一定会上街买一对亮晶晶的水钻发夹给她,要她戴上。妈妈一定是戴上了一会儿就不好意思地摘下来。那么这一对水钻夹子,不久就会变成我扮新娘的“头面”了。
父亲不久回来了,没有买水钻发夹,却带回一位姨娘。她的皮肤好细好白,一头如云的柔鬓比母亲的还要乌,还要亮。
两鬓像蝉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梳向后面,挽一个大大的横爱司髻,像一只大蝙蝠扑盖着她后半个头。她送母亲一对翡翠耳环。母亲只把它收在抽屉里从来不戴,也不让我玩,我想大概是她舍不得戴吧。
我们全家搬到杭州以后,母亲不必忙厨房,而且许多时候,父亲要她出来招呼客人,她那尖尖的螺丝髻儿实在不像样,所以父亲一定要她改梳一个式样。母亲就请她的朋友张伯母给她梳了个鲍鱼头。在当时,鲍鱼头是老太太梳的,母亲才过三十岁,却要打扮成老太太,姨娘看了只是抿嘴儿笑,父亲就直皱眉头。我悄悄地问她:“妈,你为什么不也梳个横爱司髻,戴上姨娘送你的翡翠耳环呢?”母亲沉着脸说:“你妈是乡下人,那儿配梳那种摩登的头,戴那讲究的耳环呢?”
姨娘洗头从不拣七月初七。一个月里都洗好多次头。洗完后,一个丫头在旁边用一把粉红色大羽毛扇轻轻地扇着,轻柔的发丝飘散开来,飘得人起一股软绵绵的感觉。父亲坐在紫檀木棍床上,端着水烟筒噗噗地抽着,不时偏过头来看她,眼神里全是笑。姨娘抹上三花牌发油,香风四溢,然后坐正身子,对着镜子盘上一个油光闪亮的爱司髻,我站在边上都看呆了。姨娘递给我一瓶三花牌发油,叫我拿给母亲,母亲却把它高高搁在橱背上,说:“这种新式的头油,我闻了就泛胃。”
母亲不能常常麻烦张伯母,自己梳出来的鲍鱼头紧绷绷的,跟原先的螺丝髻相差有限,别说父亲,连我看了都不顺眼。那时姨娘已请了个包梳头刘嫂。刘嫂头上插一根大红签子,一双大脚鸭子,托着个又矮又胖的身体,走起路来气喘呼呼的。她每天早上十点钟来,给姨娘梳各式各样的头,什么凤凰髻、羽扇髻、同心髻、燕尾髻,常常换样子,衬托着姨娘细洁的肌肤,袅袅婷婷的水蛇腰儿,越发引得父亲笑眯了眼。刘嫂劝母亲说:“大太太,你也梳个时髦点的式样嘛。”
母亲摇摇头,响也不响,她噘起厚嘴唇走了。母亲不久也由张伯母介绍了一个包梳头陈嫂。她年纪比刘嫂大,一张黄黄的大扁脸,嘴里两颗闪亮的金牙老露在外面,一看就是个爱说话的女人。她一边梳一边叽哩呱啦地从赵老太爷的大少奶奶,说到李参谋长的三姨太,母亲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句也不搭腔,我却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刘嫂与陈嫂一起来了,母亲和姨娘就在廊前背对着背同时梳头。只听姨娘和刘嫂有说有笑,这边母亲只是闭目养神。陈嫂越梳越没劲儿,不久就辞工不来了,我还清清楚楚地听见她对刘嫂说:“这么老古董的乡下太太,梳什么包梳头呢?”我都气哭了,可是不敢告诉母亲。
从那以后,我就垫着矮凳替母亲梳头,梳那最简单的鲍鱼头。我点起脚尖,从镜子里望着母亲。她的脸容已不像在乡下厨房里忙来忙去时那么丰润亮丽了,她的眼睛停在镜子里,望着自己出神,不再是眯缝眼儿的笑了。我手中捏着母亲的头发,一绺绺地梳理,可是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黄杨木梳,再也理不清母亲心中的愁绪。因为在走廊的那一边,不时飘来父亲和姨娘琅琅的笑语声。
我长大出外读书以后,寒暑假回家,偶然给母亲梳头,头发捏在手心,总觉得愈来愈少。想起幼年时,每年七月初七看母亲乌亮的柔发飘在两肩,她脸上快乐的神情,心里不禁一阵阵酸楚。母亲见我回来,愁苦的脸上却不时展开笑容。无论如何,母女相依的时光总是最最幸福的。
在上海求学时,母亲来信说她患了风湿病,手膀抬不起来,连最简单的缧丝髻儿都盘不成样,只好把稀稀疏疏的几根短发剪去了。我捧着信,坐在寄宿舍窗口凄淡的月光里,寂寞地掉着眼泪。深秋的夜风吹来,我有点冷,披上母亲为我织的软软的毛衣,浑身又暖和起来。可是母亲老了,我却不能随侍在她身边,她剪去了稀疏的短发,又何尝剪去满怀的愁绪呢!
不久,姨娘因事来上海,带来母亲的照片。三年不见,母亲已白发如银。我呆呆地凝视着照片,满腔心事,却无法向眼前的姨娘倾诉。她似乎很体谅我思母之情,絮絮叨叨地和我谈着母亲的近况。说母亲心脏不太好,又有风湿病。所以体力已不大如前。我低头默默地听着,想想她就是使我母亲一生郁郁不乐的人,可是我已经一点都不恨她了。因为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和姨娘反而成了患难相依的伴侣,母亲早已不恨她了。我再仔细看看她,她穿着灰布棉袍,鬓边戴着一朵白花,颈后垂着的再不是当年多彩多姿的凤凰髻或同心髻,而是一条简简单单的香蕉卷,她脸上脂粉不施,显得十分哀戚,我对她不禁起了无限怜悯。因为她不像我母亲是个自甘淡泊的女性,她随着父亲享受了近二十多年的富贵荣华,一朝失去了依傍,她的空虚落寞之感,将更甚于我母亲吧。
来台湾以后,姨娘已成了我唯一的亲人,我们住在一起有好几年。在日式房屋的长廊里,我看她坐在玻璃窗边梳头,她不时用拳头捶着肩膀说:“手酸得很,真是老了。”老了,她也老了。当年如云的青丝,如今也渐渐落去,只剩了一小把,且已夹有丝丝白发。想起在杭州时,她和母亲背对着背梳头,彼此不交一语的仇视日子,转眼都成过去。人世间,什么是爱,什么是恨呢?母亲已去世多年,垂垂老去的姨娘,亦终归走向同一个渺茫不可知的方向,她现在的光阴,比谁都寂寞啊。
我怔怔地望着她,想起她美丽的横爱司髻,我说:“让我来替你梳个新的式样吧。”她愀然一笑说:“我还要那样时髦干什么,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了。”
我能长久年轻吗?她说这话,一转眼又是十多年了。我也早已不年轻了。对于人世的爱、憎、贪、痴,已木然无动于衷。母亲去我日远,姨娘的骨灰也已寄存在寂寞的寺院中。
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是永久的,又有什么是值得认真的呢?
《素心笺》:素心笺
一、无痕暗月箋
月白撒花上衫,月白撒花散裤。
我常常记不清年月,但是却能把衣衫记得清清楚楚。就象现在,我着一身月白家居衣衫,铺开一张暗月箋。纸色昏黄,如窗外月色。字印上去,瞬时便如被云盖过般,淡淡浅浅,写过直如不写。
刚才接电话时,女儿小昭说要晚归。放下电话,我瞥见镜里,一妇人已要老去。眼尾鬓角,藏不住的风霜。
江南的梅雨季节又至,前年登梯时摔下的腿伤开始隐隐作痛。痛的是腿,不是心。
暗月箋,万事掠过,心再无痕。
二、寂寥梅花箋
藏青卡其布工装衫,藏青卡其布工装裤,黑色钢丝小发夹,三枚。
写下这张箋时,小昭只两岁。我抱着小昭再次出嫁,没有大红嫁衣,只有雪天里的梅花艳红。
彦军是好人,即使三年后我们离婚,他在我心目中仍是好人。那年月离婚的少,再嫁的更少。我一个人领着小昭,不胜其苦时,彦军娶了我。
第二次婚姻,我随着彦军走过雪天,我对着梅花说,我要好好地过。不再期待爱情,我只想要平凡的婚姻。但是我忘了,梅花是开不到春天的花朵。只有苦寒,只有苦寒。
三年后,彦军对我的猜忌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的包,被翻过;我的衣服,被嗅过;枕边屋角,都是他怀疑的起点,而怒火和拳脚是他的终点。抑或是爱到了极至,便会疑到了极至。连年幼的小昭也开始学会在大人的脸色间讨好。
缘来是恩宠,缘去却随风。我相信彦军是好人。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过去,如果不是因为他在乎我。只是我再不会去寄望一个男人,象梅花总是等不到春天。
梅花箋,花凋和泥,心无待。
三、悲喜泥金箋
大红绣花袄,大红绣花百褶裙。
依然记得第一次出嫁。喜洋洋的鞭炮,喜洋洋的亲友,还有喜洋洋的大民。
洞房花烛,我看着大民一脸的喜悦,心中有丝不忍。大民,你得到我的人,没得到我的心。
这是我生命中最平静的一段。一年不到。虽然没有爱情,但是很温暖。上晚班归家时,大民总守在巷口,回到家,还有一炉温在暖瓶里的热粥。夏天,大民三更半夜起床为我赶蚊子。我的肚子一天一天隆起来,大民贴在上面欣喜地捕捉着轻微的胎动。有时候我几乎忘了,我本不爱大民。而我也开始相信,这样的日子真的可以平安长久。
直到小昭出世。
小昭,小昭。大民不再做游戏的主角,他第一次打了我。掌痕印在我的脸上,我看到的却是他掩不住的颤抖和苦楚。
小昭满月后,大民走了,走得很远。
大民的眼睛里有泪痕,但是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大民,我如何对得起你。
这一场婚姻,来得快,去得太快。来去间,悲喜间,是错。
泥金箋,悔错处。
四、风月燕子箋
鹅黄小碎花棉布连衣裙,白色搭襻凉鞋。
二十岁,我听到琴音。那是简陋的年代,一支口琴已经弥足珍贵。何况会吹琴的人。
他轻轻踏着节拍,在夕阳里吹着琴。晚风,春柳,春心。
我知道他较我年长,家中娇妻幼子,只是我神摇心旌。情深处,以一夕换一生又何妨。甜蜜时,我想我愿是飞蛾;如那纤体的小昆虫,燃过了,一切再不足惜。
他常常吹起琴来,我散漫地吟唱,我的手并入他的手,便再没有别的地老天荒。
这样的日子本来可以很久,本来可以很长,只可惜双飞双宿不过是梦一场。
郎心似铁,恩爱瞬时绝。梁上燕,衔不去我的思念。心若是可以收藏,我早已把心熨平了,折叠了,压箱底地藏。只是那熨过处,依然是折痕累累,是曾经的誓言曾经的泪水曾经的伤痛,烙身附体般难消难灭。
燕子箋,偕手相看处,已成过往。
五、箋外语
我是小昭。今年十八岁。
我没见过父亲,父亲在得知母亲怀孕后就抛弃了她。
我后来见过大民叔叔,他是个好人。母亲与大民叔叔结婚八个月,誔下足月的我。大家都说是母亲欺骗了他,但是在那个婚内打胎需要单位证明、婚外更要追究作风问题的年代,母亲也有母亲的可怜。
我不太喜欢凶凶的爱打人的彦军叔叔,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我和母亲现在是两人的生活,两人过。
《素心笺》:故乡的桂花雨
中秋节前后,就是故乡的桂花季节。一提到桂花,那股子香味就彷佛闻到了。桂花有两种,月月开的称木樨,花朵较细小,呈淡黄色,台湾好像也有,我曾在走过人家围墙外时闻到这股香味,一闻到就会引起乡愁。另一种称金桂,只有秋天才开,花朵较大,呈金黄色。我家的大宅院中,前后两大片旷场,沿着围墙,种的全是金桂。惟有正屋大厅前的庭院中,种着两株木樨、两株绣球。还有父亲书房的廊檐下,是几盆茶花与木樨相间。
小时候,我对无论什么花,都不懂得欣赏。尽管父亲指指点点地告诉我,这是凌霄花,这是叮咚花,这是木碧花。我除了记些名称外,最喜欢的还是桂花。桂花树不像梅花那么有姿态,笨笨拙拙的,不开花时,只是满树茂密的叶子,开花季节也得仔细地从绿叶丛里找细花,它不与繁花斗艳。可是桂花的香气味,真是迷人。迷人的原因,是它不但可以闻,还可以吃。“吃花”在诗人看来是多么俗气,但我宁可俗,就是爱桂花。
桂花,真叫我魂牵梦萦。
故乡是近海县分,八月正是台风季节。母亲称之为“风水忌”。桂花一开放,母亲就开始担心了:“可别做风水啊!”(就是台风来的意思。)她担心的第一是将收成的稻谷,第二就是将收成的桂花。桂花也像桃梅李果,也有收成呢。母亲每天都要在前后院子走一遭,嘴里念着:“只要不做风水,我可以收几大箩。送一斗给胡宅老爷爷,一斗给毛宅二婶婆,他们两家糕饼做得多。”原来桂花是糕饼的香料。桂花开得最茂盛时,不说香闻十里,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桂花成熟时,就应当“摇”,摇下来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鲜,如任它开过谢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雨吹落,那就湿漉漉的,香味差太多了。“摇桂花”对于我是件大事,所以老是钉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嘛?”母亲说:“还早呢,没开足,摇不下来的。”可是母亲一看天空阴云密布,云脚长毛,就知道要“做风水”了,赶紧吩咐长工提前“摇桂花”,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篾簟,帮着抱桂花树使劲地摇,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母亲洗净双手,撮一撮桂花放在水晶盘中,送到佛堂供佛。父亲点上檀香,炉烟袅袅,两种香混和在一起,佛堂就像神仙世界。于是父亲诗兴发了,实时口占一绝:“细细香风淡淡烟,竞收桂子庆丰年。儿童解得摇花乐,花雨缤纷入梦甜。”诗虽不见得高明,但在我心目中,父亲确实是才高八斗,出口成诗呢。
桂花摇落以后,全家动员,拣去小枝小叶,铺开在簟子里,晒上好几天太阳,晒干了,收在铁罐子里,和在茶叶中泡茶,做桂花卤,过年时做糕饼。全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
念中学时到了杭州,杭州有一处名胜满觉珑,一座小小山坞,全是桂花,花开时那才是香闻十里。我们秋季远足,一定去满觉珑赏桂花。“赏花”是借口,主要的是饱餐“桂花栗子羹”。因满觉珑除桂花以外,还有栗子。花季栗子正成熟,软软的新剥栗子,和着西湖白莲藕粉一起煮,面上撒几朵桂花,那股子雅淡清香是无论如何没有字眼形容的。即使不撒桂花也一样清香,因为栗子长在桂花丛中,本身就带有桂花香。
我们边走边摇,桂花飘落如雨,地上不见泥土,铺满桂花,踩在花上软绵绵的,心中有点不忍。这大概就是母亲说的“金沙铺地,西方极乐世界”吧。母亲一生辛劳,无怨无尤,就是因为她心中有一个金沙铺地、玻璃琉璃的西方极乐世界。
我回家时,总捧一大袋桂花回来给母亲,可是母亲常常说:“杭州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旧宅院子里的金桂。”
于是我也想起了在故乡童年时代的“摇花乐”,和那阵阵的桂花雨。
《素心笺》:水之源
今日之前的秋,连着几天,早晚略有一丝凉意,白天仿佛错回了夏。太阳白亮亮的,地面热腾腾的。人即便穿着短袖也汗津津的,像被热气蒸腾的馒头。就是这样的几天,无论我行到哪里,坐在何方,都逃不过桂花的香醺。
那日,在厨房忙活,即便锅里“吱吱啦啦”飘出扁豆红烧肉的味道,鼻翼仍不觉被窗外不远处几株桂花树的香气煽动,惹得我边烧菜边偶尔转头张望。
外出的时候,沿着小区的人行道,热风中弥漫着鳞次的桂花树香。上了公交车,车子行走的长江西路,亦是一路鳞次的桂花树,这些马路上的桂花香,混合着汽车排除的尾气、大商小贩们秋令食物果品的香气,再有白领蓝领男人女人老人小孩的体味,扑进车厢。尽管被混杂,桂花的香气还是令人格外在意。车厢里,不时有女孩子的惊讶声“哎呀!桂花好香!呆会儿停下摘一枝!”
女孩子的话着实让我心动。昏沉沉靠在座位上的我,心想着,校园专家楼背面有一个硕大的桂花树,是否经过时摘一枝呢?一转念,似乎不妥。记得去年桂花飘香的季节,傍晚时分,有几个女生摘桂花,我刚好经过,很想让女生匀一枝给我。念头如此,而身为学校职工的我,嘴上不得不说:“同学们,还是不要摘的好,这株桂树很多年了,起码我进校时就有了。大家你一枝我一枝,桂树迟早会消瘦的。”几个女生红着脸,朝我使劲地点着头,又掩饰不住兴奋地举着饱满的桂花枝跑走了。望着跑远的女生的背影,我心里好生羡慕她们的冲动。谁都经过冲动的年纪,曾几何时,青春的我,大学时代的宿舍里也曾点缀过偷偷摘来的花枝。
因连着几日醺在桂花香里,亦因爱上涂鸦琐碎文字,便咨询了对花草有栽培经验的邻家伯伯。伯伯告诉我,中秋前后天气突然热起来,竟像夏季一样,桂花一经蒸郁,就烂烂漫漫地盛开了。这种早晚冷凉、白天燠热的天气既有利于桂树的营养积累,也促使雨露的形成,桂树开花随之加速,苏州人称之为“桂花蒸”。
桂花蒸!桂花蒸!最近迷张爱铃的我,顿然想起她的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秋是一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调,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炎樱”,“丁阿小手牵着儿子百顺,一层一层楼爬上来。高楼的后阳台上望出去,城市成了旷野,苍苍的无数的红的灰的屋脊,都是些后院子,后窗,后巷堂,连天也背过脸去了,无面目的阴阴的一片,过了八月节还这么热,也不知它是什么心思。”当初草看这篇,尚不明了“桂花蒸”的含意。原来如此。懂了桂花蒸的意思,再读张的小说,似心有灵犀,不觉兀自地笑了起来。
“冷露无声湿桂花”,“露密前山桂”,“天将秋气蒸寒馥,月借金波摘子黄”,“重露湿香幽径晓,斜阳烘蕊小窗妍”。古诗中“冷露”、“露密”说明桂树开花天气要早晚冷凉;“烘与蒸”说明天气还会一度出现较高的温度。想来愈发仰慕古代的文人骚客,他们作诗言物,竟将这不慎稀罕的桂树桂花的禀性惟妙惟肖凝炼出来,正所谓三两句诗词胜千万语长论。
又是一年桂花开,桂花香醺无处逃。今年此时,因寻着桂之精髓,桂花的香里更似比往年多了些许禅道。停笔之时,一场秋雨刚过,天凉了。还是同样的路线,经过,桂香淡了。好在桂香浓郁时,我为她留了心。
“乘凉仿佛是隔年的事了。”当年如此,此刻恰好亦同感。
《素心笺》:下雨天,真好
我问你,你喜欢下雨吗?你会回答说:“喜欢,下雨天富于诗意,叫人的心宁静,尤其是夏天,雨天里睡个长长的午觉该多舒服。”可是你也许会补充说:“但别下得太久,像那种黄梅天,到处湿漉漉的,闷得叫人喘不过气来。”
告诉你,我却不然。我从来没有抱怨过雨天,雨下了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屋子里挂满万国旗似的湿衣服,墙壁地板都冒着湿气,我也不抱怨。我爱雨不是为了可以撑把伞兜雨,听伞背滴答的雨声,就只是为了喜欢那下不完雨的雨天。为什么,我说不明白,好像雨天总是把我带到另一个处所,离这纷纷扰扰的世界很远很远。在那儿,我又可以重享欢乐的童年,会到了亲人和朋友,游遍了魂牵梦萦的好地方。悠游、自在。那些有趣的好时光啊,我要用雨珠的链子把它串起来,绕在手腕上。
今天一清早,掀开帘子看看,玻璃上已洒满了水珠,啊,真好,又是个下雨天。
守着窗儿,让我慢慢儿回味吧。我那时才六岁呢,睡在母亲暖和的手臂里,天亮了,听到瓦背上哗哗哗的雨声,我就放心了。因为下雨天长工不下田,母亲不用老早起来做饭,可以在热被窝里多躺会儿。这一会儿工夫,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我舍不得再睡,也不让母亲睡,吵着要她讲故事。母亲闭着眼睛,给我讲雨天的故事。有一个瞎子,雨天没有伞,一个过路人看他可怜,就打伞一路送他回家,瞎子到了家,却说那把伞是他的,还请来邻居评理,说他的伞有两根伞骨是用麻线绑住的,伞柄有一个窟窿。说得一点也不错。原来他一面走一面用手摸过了,伞主人笑了笑,就把伞让给他了。我说这瞎子好坏啊!母亲说,不是坏,是因为他太穷了,伞主想他实在应当有把伞,才把伞给他的,伞主是个好心人。在曦微的晨光中,我望着母亲的脸,她的额角方方正正,眉毛是细细长长的,眼睛也眯成一条线。教我认字的老师说菩萨慈眉善目,母亲的长相大概也跟菩萨一个样子吧。
雨下得愈大愈好,檐前马口铁落水沟叮叮地响,我就合着节拍唱起山歌来。母亲一起床,我也就跟着起来,顾不得吃早饭,就套上叔叔的旧皮靴,顶着雨在院子里玩。阴沟里水满了,白绣球花瓣飘落在烂泥地和水沟里。我把阿荣伯给我雕的小木船漂在水沟里,中间坐着母亲给我缝的大红“布姑娘”。绣球花瓣绕着小木船打转,一起向前流。我跟着小木船在烂泥地里踩水,吱嗒吱嗒地响。直到老师来了才被捉进书房。可是下雨天老师就来得晚,他有脚气病,像大黄瓜的肿腿,穿钉鞋走田埂路不方便。我巴不得他摔个大筋斗掉在水田里,就不会来逼我认方块字了。
天下雨,长工们就不下田,都蹲在大谷仓后面推牌九。我把小花猫抱在怀里,自己再坐在阿荣伯怀里,等着阿荣伯把一粒粒又香又脆的炒胡豆剥了壳送到我嘴里,胡豆吃够了再吃芝麻糖,嘴巴干了吃柑子。肚子鼓得跟蜜蜂似的。一双眼睛盯着牌九,黑黑的四方块上白点点,红点点。大把的铜子儿一会儿推到东边,一会儿推到西边。谁赢谁输都一样有趣。我只要雨下得大就好,雨下大了他们没法下田,就一直这样推牌九推下去。老师喊我去习大字,阿荣伯就会去告诉他:“小春肚子痛,喝了午时茶睡觉了。”老师不会撑着伞来谷仓边找我的。母亲只要我不缠她就好,也不知我是否上学了,我就这么一整天逃学。下雨天真好,有吃有玩,长工们个个疼我,家里人多,我就不寂寞了。
潮湿的下雨天,是打麻线的好天气,麻线软而不会断。母亲熟练的双手搓着细细的麻丝,套上机器,轮轴呼呼地转起来,雨也跟着下得更大了。五叔婆和我帮着剪线头,她是老花眼,母亲是近视眼,只有我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最管事。为了帮忙,我又可以不写大小字。懒惰的四姑一点忙不帮,只伏在茶几上,唏呼唏呼抽着鼻子,给姑丈写情书。我瞄到了两句:“下雨天讨厌死了,我的伤风老不好。”其实她的鼻子一年到头伤风的,怨不了下雨天。
五月黄梅天,到处黏塌塌的,母亲走进走出地抱怨,父亲却端着宜兴茶壶,坐在廊下赏雨。院子里各种花木,经雨一淋,新绿的枝子,顽皮地张开翅膀,托着娇艳的花朵。冒着微雨,父亲用旱烟管点着它们告诉我这是丁香花,那是一丈红。大理花与剑兰抢着开,木樨花散布着淡淡的幽香。墙边那株高大的玉兰花开了满树,下雨天谢得快,我得赶紧爬上去采,采了满篮子送左右邻居。玉兰树叶上的水珠都是香的,洒了我满头满身。
唱鼓儿词的总是下雨天从我家后门摸索进来,坐在厨房的条凳上,咚咚咚地敲起鼓子,唱一段秦雪梅吊孝,郑元和学丐。母亲一边做饭,一边听。泪水挂满了脸颊,拉起青布围裙擦一下,又连忙盛一大碗满满的白米饭,请瞎子先生吃,再给他一大包的米。如果雨一直不停,母亲就会留下瞎子先生,让他在阿荣伯床上打个中觉,晚上就在大厅里唱,请左邻右舍都来听。大家听说潘宅请听鼓儿词,老老少少全来了。宽敞的大厅正中央燃起亮晃晃的煤气灯,发出嘶嘶嘶的声音。煤气灯一亮,我就有做喜事的感觉,心里说不出的开心。大人们都坐在一排排的条凳与竹椅上,紫檀木镶大理石的太师椅里却挤满了小孩。一个个光脚板印全印在茶几上。雨哗哗地越下越大,瞎子先生的鼓咚咚地也敲得愈起劲。唱孟丽君,唱秦雪梅,母亲和五叔婆她们眼圈都哭得红红的,我就只顾吃炒米糕、花生糖。父亲却悄悄地溜进书房作他的“唐诗”去了。
八九月台风季节,雨水最多,可是晚谷收割后得靠太阳晒干。那时没有气象报告,预测天气好坏全靠有经验的长工和母亲抬头看天色。云脚长了毛,向西北飞奔,就知道有台风要来了。我真开心。因为可以套上阿荣伯的大钉鞋,到河边去看涨大水。母亲皱紧了眉头对着走廊下堆积如山的谷子发愁,几天不晒就要发霉的呀,谷子的霉就是一粒粒绿色的曲。母亲叫我和小帮工把曲一粒粒拣出来,不然就会愈来愈多的。这工作好好玩,所以我盼望天一直不要晴起来,曲会愈来愈多,我就可以天天滚在谷子里拣曲,不再读书了。母亲端张茶几放在廊前,点上香念太阳经,保佑天快快放晴。太阳经我背得滚瓜烂熟,我也跟着念,可是从院子的矮墙头望出去,一片迷蒙。一阵风,一阵雨,天和地连成一片,看不清楚,看样子且不会晴呢,我愈高兴,母亲却愈加发愁了。母亲何苦这么操心呢。
到了杭州念中学了,下雨天就可以坐叮叮咚咚的包车上学。一直拉进校门,拉到慎思堂门口,下雨天可以不在大操场上体育课,改在健身房玩球,也不必换操衣操裤。我最讨厌灯笼似的黑操裤了。从教室到健身房有一段长长的水泥路,两边碧绿的冬青,碧绿的草坪,一直延伸到健身房后面。同学们起劲地打球,我撑把伞悄悄地溜到这儿来,好隐蔽,好清静。我站在法国梧桐树下,叶子尖滴下的水珠,纷纷落在伞背上,我心里有一股凄凉寂寞之感,因为我想念远在故乡的母亲。下雨天,我格外想她。因为在幼年时,只有雨天里,我就有更多的时间缠着她,雨给我一份靠近母亲的感觉。
星期天下雨真好,因为“下雨天是打牌天”,姨娘讲的。一打上牌,父亲和她都不再管我了。我可以溜出去看电影,邀同学到家里,爬上三层楼“造反”,进储藏室偷吃金丝蜜枣和巧克力糖,在厨房里守着胖子老刘炒香喷喷的菜,炒好了一定是我吃第一筷。晚上,我可以丢开功课,一心一意看《红楼梦》,父亲不会衔着旱烟管进来逼我背《古文观止》。稀里哗啦的洗牌声,夹在洋洋洒洒的雨声里,给我一万分的安全感。
如果我一直不长大,就可一直沉浸在雨的欢乐中。然而谁能不长大呢?人事的变迁,尤使我于雨中俯仰低徊。那一年回到故乡,坐在父亲的书斋中,墙壁上“听雨楼”三个字是我用松树皮的碎片拼成的。书桌上紫铜香炉里,燃起了檀香。院子里风竹萧疏,雨丝纷纷洒落在琉璃瓦上,发出叮咚之音,玻璃窗也砰砰作响。我在书橱中抽一本白香山诗,学着父亲的音调放声吟诵,父亲的音容,浮现在摇曳的豆油灯光里。记得我曾打着电筒,穿过黑黑的长廊,给父亲温药。他提高声音吟诗,使我一路听着他的声音,不会感到冷清。可是他的病一天天沉重了,在淅沥的风雨中,他吟诗的声音愈来愈低,我终于听不见了,永远听不见了。
杭州的西子湖,风雨阴晴,风光不同,然而我总喜欢在雨中徘徊湖畔。从平湖秋月穿林***走向孤山,打着伞慢慢散步。心沉静得像进入神仙世界。这位宋朝的进士林和靖,妻梅子鹤,终老是乡,范仲淹曾赞美他“片心高与月徘徊,岂为千钟下钓台。犹笑白云多自在,等闷因雨出山来。”想见这位大文豪和林处士徜徉林泉之间,留连忘返的情趣。我凝望着碧蓝如玉的湖面上,低斜的梅花,却听得放鹤亭中,响起了悠扬的笛声。弄笛的人向我慢慢走来,他低声对我说:“一生知己是梅花。”
我也笑指湖上说:“看梅花也在等待知己呢。”雨中游人稀少,静谧的湖山,都由爱雨的人管领了。衣衫渐湿,我们才同撑一把伞绕西泠印社由白堤归来。湖水湖风,寒意袭人。站在湖滨公园,彼此默默相对。“明亮阳光下的西湖,宜于高歌;而烟雨迷蒙中的西湖,宜于吹笛。”我幽幽地说。于是笛声又起,与潇潇雨声相和。
二十年了,那笛声低沉而遥远,然而我,仍然依稀听见,在雨中……
琦君简介——琦君(1916年7月24日—2006年6月7日),1916年7月24日生于温州的瓯海瞿溪乡,原名潘希珍,又名潘希真,小名春英,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人。现当代台湾女作家,14岁就读于教会中学。1949年赴台湾,在司法部门工作了26年,并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定居美国。琦君以撰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她的名字总是与台湾散文连在一起。代表作品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30余种,包括《烟愁》《红纱灯》(获中山文艺创作奖)《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琦君寄小读者》《琴心》《菁姐》《七月的哀伤》以及《琦君自选集》等等。她也是著名电视剧《橘子红了》的原作者。2006年6月7日凌晨4时45分病逝于和信医院,享年90岁。
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幽幽的怆痛。1949年的大迁徙、大分裂,使得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都遭罹了一番“失乐园”的痛楚,思乡怀旧便很自然地成为他们主要的写作题材了。林海音写活了老北京的“城南旧事”,而琦君笔下的杭州,也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还有更多的优美的散文在等着你去欣赏】>>>点击进入
如果您有好的作品,您也可以点击下方“我要投稿”把您的作品发给我们,届时将会让更多的观众欣赏到您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