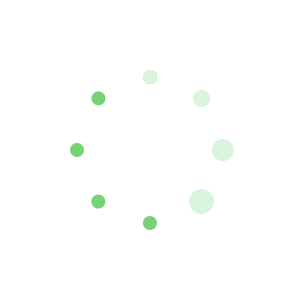当我无聊的时候,会站在挪威的商业大楼里廊言大喊,面对眼中那些皆平剩面世俗的视角,仿佛扬荡起的空气中沉默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内心声在呐喊徘徊着,我想,那是我的灵魂在跟我对话了。
以前懵懂的我不懂得什么是亲情,什么是爱情?
自打幼小如物出生后,便注定了青春与我两间的骅然相守又直到岁月的暗柳陈苍,恐怕我现在对于暗柳陈苍之类的早话还殊途为陌,为今过早了些,青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算不算是经历风雨前的彩虹呢,迄今为止,每人都有一说。
记得五六岁当自己还是初发萌芽的阶段时期时,那时我早早拥有了人类的七情六欲中的其欲嫉妒,在那些淡淡夏州的夜晚,和奶奶弟弟同床共睡的我,几乎睡眠不怎么入眠,如不是每晚睡虫在作祟,我怎会瞧见奶奶一只手伸进弟弟的背衣衫里轻饶地抓阄着,年幼的弟弟彻夜忽睡忽醒娇气的要求奶奶一抓痒背,榆次同时背痒欠饶的我,奶奶反眼视之不理,倒将瘦如柴骨地老手慈祥的摸进弟弟的背囊中摸麻抚语着,我试睁着一双无辜埋怨的大眼睛干渴姚望着奶奶迷蒙的双眼,与两面游离在间的手背,那只老粗而稍显发黑的手背上有着许多青筋,在我彻绵帘绝下犹略可见,那是久久无情岁月摧残过后留下的最后一抹柳尾,而我就是盼望着这最后的柳尾能够多分我一点儿那就好了,这就是这样一个卑微不屈的希望,哪怕只有一丁点儿,这就叫作“年幼”了吧,偶尔早期出现过的年幼都是从这儿涛涛罗逸的天际中发出的,总而久之,正忧思鸣苦的我就是这么理解过来的。
孤寂无眠的夜影还死死抓着我忧楚的思绪不放,脑袋中空洞的时钟在不停繁衍的响起促使我眼中的泪花妒掩而欲啼流,哀哀丝丝地低泣声在月照独窗的情澜下潮起又潮落,奶奶的眉头间稍微皮皱了当下,形成了一条很不平衡的天坪线徒挂眼边,在她不耐烦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历往传今以来再乘女奴的阶级世椅,自古当人是男重女轻的大时代,而如今以往男人过去的辉煌历史倒过了现在的女英骑在当下的趋势传奇,为什么别人可以享受今有的荣誉,而我为什么就不能够在家里厚读那些传奇呢。
于此于词,奶奶对我的疼爱比以前减少甚去了些,能造成这样的后果,也是因为我每晚的不屈不饶和想尽办法的折磨人。
后来我长到了十岁时,我们三个人同床共枕的缘分就渐渐分散了,奶奶去乡下老家跟爷爷挤挨挤着生活去了,而家里就老是隐隐传散出另约的不爽快,他非常不满妈妈平日为人做事那些富商原则,所以有好几个宁静的夜晚,我都能听到他们话对话的吵架声音。
其实听多了,也就习惯了。
晚自习间,我从书包里翻出一本漫画书,兴致扶绕的看,而不是拿了个像样的练习课本复习功课,旁边,弟弟的手里抱着不知从哪里来的破车破弹珠,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就好奇的问他,听他说,就是在放学的路上意外捡到的,看见这些东西好看又好玩,所以就偷偷摸摸带了回家。我嘲笑他没有出息,连别人扔掉不要的东西也要,对于我的种种讽刺,一向沉默寡言的他却不带任何风云的变幻说,“你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人,我才不跟你一般见识呢。”哪儿知道,在他严密紧实的嘴巴下吐出了这么令人不快的言语,当即,我狠狠拿脚踹了他的肚皮一下,在脾气爆发的边缘上,我根本没在乎他是不是我弟弟,只知道惹了我生气的人,就会是这样悲惨的下场,但除了我的爸爸和妈妈。
没过一会儿,在客厅好好看着电视剧的两位大人冲进了房间,进来之后,就马上看到弟弟那种泪流满面的可怜模样,我站在旁边,不顾爸妈的存在,还狠狠地瞪着他一番。
大不了被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就算了,有什么好可怕的。
我就在抱着这种认死的想法下被妈妈拖进了另一间房间,进去之前和进去之后的我却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
这天晚上,我和弟弟都没有睡着,各自都在想着自己的事情。